青年法学家苏宇:风尘仆仆的未来法治
青年法学家苏宇:风尘仆仆的未来法治

人物简介
苏宇,1985年出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数据法学研究院院长、数据法学学科带头人。曾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篇,获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科研杰出贡献奖等荣誉,被表彰为全国公安优秀教师,入选北京市法学会“百名法学英才”。
这束光终将洞穿整个时代
2017年12月,我在上海偶然听到了“区块链”这个词。当时,我恐怕是法学“青椒”(网络用语,指大学青年教师)圈里接触区块链比较晚的一员了。哈希、“双花”、分片、侧链、共识机制、闪电网络、链基治理……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区块链概念和架构设计扑面而来。这是一片我难以想象的“海洋”。我意识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许多机制和秩序的底层逻辑将会被改写,而法学人在其中有不可推卸的使命。
一回到北京,我就将正在撰写的《行政法简史》一书的书名改成了《行政法的历史与未来》,还给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安装了编程软件,疯狂地补课。自从高三那年冬天结束“信奥”(指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之旅后,我就成为一名文科生。从大学二年级至今,我已经13年没有写过代码了。
我一边学习,一边主动“求开会”。那两年,我经常风尘仆仆地赶往清华园参加相关学术会议,有学友安排的当然最好,如果没有门路,我就想方设法地混进去。要是会场内座无虚席,我就找一块尽可能接近与会者的空地坐下,因为要记很长时间的笔记。在必须出差时,无论在火车站还是候机室,我也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编程和学习技术原理的机会,把行李箱横着一放就是个桌面,笔记本电脑只要有电就行。
在这片“海洋”里,我所见的一切都是崭新的:除了区块链,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度学习也令人着迷,人工神经网络的耀眼光芒更让人无法视而不见。我感觉,这束光终将洞穿整个时代。
从零星起步到遍地开花
其实,那时的法学界已经有很多“早行人”了。《法律科学》杂志2017年第5期的那个专栏可能会被很多人铭记——一次性刊发了5篇研究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论文。5年后,这5篇论文在中国知网记录到的总被引数已超过3600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梅夏英在2016年就发表了《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一文;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的《区块链与未来法治》一文也于2018年春天见刊;至于个人信息保护研究,早在2013年左右就可谓热潮初现。几乎在所有相关主题的会议上都会有人说“未来已来”。随着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的成立,“未来法治”这个概念越发被人们所熟知。
那时学界刚开始热议的“代码2.0”“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等概念,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至于网络信息法学、计算法学、数据法学的概念,虽然在含义上有广狭之分,但那时也早已出现。很快,“数字法学”也隆重“登场”。大量的高等院校成立非在编的科研机构,西南政法大学甚至建立了实体化的人工智能法学院。这一切令人目不暇接。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靠“搬运”和组合域外研究成果已经无法应对数字法治的新需求,直面难题的自主探索势在必行。除了技术基础的不断充实,学者们依托的“阵地”也不断升级,“有组织科研”的脚步声已在数字法学领域响起。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数据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矜婷在多个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法学教研中心数字法学实验室的建设情况,巨大体量的数据和精准的数据分析功能令其他高校的与会者艳羡不已。部分年轻学者也开始建设自己的实验室或频繁访问同事的实验室。跨学科的团队合作研究在数字法学领域蔚然成风。在中国政法大学,已经有至少两位法学教师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计算机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跨学科合作论文;而对法律现象进行数据分析和量化实证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
潜入数字法学研究的“深水区”
在数字洪流的席卷下,这个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如果说星辰大海已在眼前,那么对于身处其中的法学人来说,这却很可能是一场越来越吃力的“野泳”。信息技术浪潮中的法学人经常需要就一知半解的问题发表观点。谈论区块链的可能搞不清楚不对称加密和布隆过滤器,谈论人工智能的可能搞不清楚梯度和最大似然估计,谈论数据安全的可能搞不清楚信息熵和推理通道,但研究仍然在继续;而在相对可以更专注于研究法律问题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平台治理方面,更是迎来了潮水般的研究成果。眼前的景象似乎更像一片海滩:沙滩上人满为患,浅水区时有喧嚣,但一望无际的深水区却人迹罕至。
数字洪流催生了“数字法学”的繁荣,但也有可能让法学人在规则形成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失能”。技术专家对行政立法的影响正在显著加强,对数字法学的影响也在逐渐体现。法学人如果不想人云亦云、全盘接受技术专家抛出的结论,就只能自己扎进技术文献和代码堆中一探究竟;在技术文献中盘桓日久,又会逐渐接触这场变革的底层数理逻辑。难以想象,如今的我会经常提及顾险峰、孙增圻、张拳石等技术专家的见解——十年前,这些名字可能是汉斯·凯尔森、施密特·阿斯曼或皮特·L.施特劳斯,全都是公法学家。当然,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创见,以后还可能会不时在我某个幽微的思想深处交汇。
创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数据法学研究院以后,我对新兴领域的法治问题研究日益深入。人在中年阶段转型本来就颇为不易,很难在探索新兴领域的同时,再去做《权力概念的变迁与反思》这样的研究了。这可能也是不少同龄法学人的共同体验。数据和算法领域的中外立法、标准制定、政策发布、形势变化等让人目不暇接,新技术带来的新兴法律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闻所未闻的挑战让人措手不及。
法律与科技:在“互动”中共同发展
2016年,法学界只需要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基础知识;2019年以后,就必须面对多头注意力机制的强势崛起。2017年谈论区块链时,还更多地聚焦于比特币和工作量证明;到 2021年,就需要琢磨信标链和分布式金融。
这些技术的变化虽然对法律关系的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但是也并非毫无法律意义。例如,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研究者往往会提及“用户画像”,但如果企业采用基于用户行为的协同过滤技术来给用户推荐商品,而不是直接向用户要信息、给用户贴“标签”,那么相关研究者就需要对此进行更充分的研究。算法治理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强调算法的可解释性,深度神经网络往往是算法“黑箱”的最佳例证,但Transformer(一个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深度学习模型)的自解释能力就强得多,对附加解释机制的要求也不同。这些技术对法律关系的影响是间接而深远的,如果法学人对技术的关注跟不上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没有充分关注到技术路线的快速演化和业态的变革,那么提出来的治理对策和制度方案将可能驴唇不对马嘴。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未来法治”的研究被技术、应用和产业的浪潮不断推着往前走:数据交易市场的兴起让数据权属问题成为焦点;深度合成技术的流行推动着相关规则的研讨和制定;数字藏品的火热“预订”了非同质通证研究成果的需求。
作为这一领域最有潜力的新锐学者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在 2022年发表了10篇论文和1篇译文,内容横跨数据销毁、隐私计算、数据跨境传输和“元宇宙”风险治理等多个领域。各个细分领域都出现了大量的新机遇,不少年轻学者选择了相对聚焦的研究领域,如张欣和张恩典聚焦算法治理、马颜昕和宋烁聚焦公共数据、郑曦和裴炜聚焦刑事诉讼中的数据问题等。即便是著名的基础理论研究专家,也不得不关注新兴信息技术对法治的影响和冲击,因为它已无处不在,我们必须面对“数字化生存”的现实。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风险的关注,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对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告知同意规则的研究都是典型实例。
面对无处不在的新选题、新需求、新挑战,风尘仆仆的“未来法治”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上都呈现紧锣密鼓的态势。法学人可以接触的选题几乎无限丰富,但平坦易行的道路上早已人满为患,每个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选题都充满挑战。
2023年,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数据权属问题、数据安全问题、算法治理问题、平台监管问题等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每个尚未解决的细分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难题:数据分类分级所需要梳理的数据种类、体量、风险和场景,数据权益配置所面对的相关收益界定和分配复杂性程度,监管科技的精准合理应用,自动化行政过程中的数据埋点和审计轨迹管理,等等。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原先看起来十分困难的问题也逐渐水落石出。例如,算法“黑箱”的打开和算法透明度的实现问题,曾经在研究者的眼中也是荆棘丛生。如今,我们已经可以逐步聚焦到Shapley值法(一种来自合作博弈论的计算方法)和反事实解释等具有重要法律意义和技术价值、需要重点关注的解释方法了。从遍布学术舶来品的会场到全方位自主研究和解决问题,短短几年,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条非常不容易的道路。
拓荒前行,奔赴未来法治
与传统法学领域不同,数字法学的研究显得更加生意盎然。这不仅是因为技术、应用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知识、制度和学说的不断更新换代,也是因为数字法学的研究并不需要在无垠的故纸堆中上下求索,即不太需要资历的支撑,对法学“青椒”天然友好,更是因为这一领域没有所谓的“权威”模板和现成答案,我们只能自己寻求解题之道。其他国家或地区和我们基本上同时迎接新需求、新挑战,许多问题他们也还在摸索之中,这对于本土的学术创新而言无疑是宝贵的机遇。
在林林总总的研究热潮中,一条主线逐渐清晰可见。面对数字时代的来临,捍卫人的主体性地位正在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目标。保障数字社会和信息技术洪流中的人的尊严、增强人的“数字化生存”能力,使普通人远离“失能”困境而重获宝贵的自主性,已经越来越成为许多法学人所关切的价值基点:“法律制度应思考技术给人的主体性地位乃至人类命运带来的巨大后果”,重要的是“避免人主体性的消解和自治性的丧失”。
法治的活力往往在于权利的“牙齿”生长到什么程度,在数字世界中,为普通人“赋权”和“赋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一研究进路已经在平台层、数据层和算法层中全面展开,未来,这条主线或将在以技术性正当程序、智能化适老服务、个人敏感信息保护等重要议题上熠熠生辉,也将和世界范围内的前沿学说、主张交相辉映。
同时,我们要关注那些人迹罕至的“水域”。在数字法研究的热浪中,有些主题已经是“极热”。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开放、算法解释权等。而有些主题仍然需要更充分的关注和投入。例如,云计算领域的相关立法及算法审计机制、数据污染治理、数据安全评估制度等议题,每一项在未来法治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每一项也都迫切需要进行扎实的科研攻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欣喜地看到中国数字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在这些议题上的一系列独到贡献。
本文载于《法律与生活》杂志2023年1月刊
来源:法律与生活杂志
-

- 漫谈:巴斯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的性格特点及王位的取得过程
-
2025-09-03 22:00:49
-

- 河北男子恋爱不成入室行凶,被女孩反杀,法院正义审判大快人心
-
2025-09-03 21:58:34
-

- 刘备一生没重用赵云,临死前才告诉他为什么:你有三件事办砸了!
-
2025-09-02 21:51:29
-

- 从历史中追寻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到底什么是大英帝国?
-
2025-09-02 21:49:1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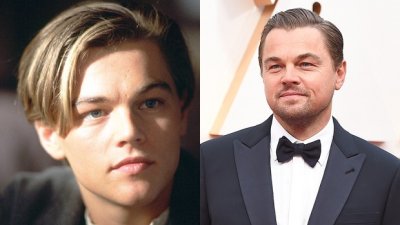
- 《泰坦尼克号》演员23年后的变化,谁变化最大
-
2025-09-02 21:46:58
-

- “十四五”交卷年,这些绿色信号不容错过
-
2025-09-02 21:44:4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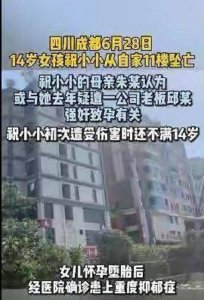
- 2017年,台湾女作家在家中自杀,读者从其作品中发现过往悲惨遭遇
-
2025-09-02 21:42:2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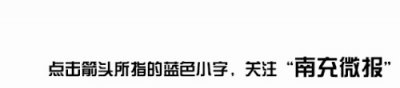
- 对答案啦!2019四川高考试题+答案公布(完整版)
-
2025-09-02 21:40:11
-

- 浙报专版刊登:同向同行画好最大同心圆 敢闯敢干共绘精彩团结篇——2024年浙
-
2025-09-02 21:37:55
-

- 傅丽莉:嫁给孙淳36年,64岁坚持丁克,夫妻俩花60万养只狗当儿子
-
2025-09-02 21:35:3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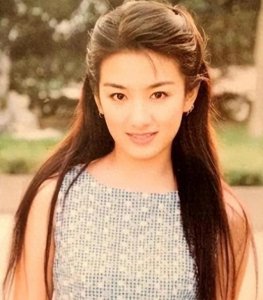
- 事实证明,“过气女星”的黄奕,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康庄大道
-
2025-09-02 21:33:23
-

- 15位演过虞姬的女演员,看过才知道,啥叫倾国倾城,啥叫丑不自知
-
2025-09-02 21:31:07
-

- 朝鲜战争风云:中美俄朝韩五国教科书,分别如何叙述这场战争?
-
2025-09-02 21:28:51
-

- 为什么会爆发中越战争?
-
2025-09-02 21:26:3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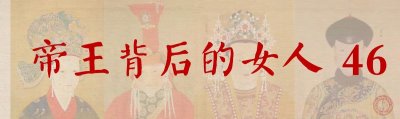
- 康熙帝惠妃:位列四妃之首,并非明珠妹妹,跌宕半生仍得高寿而终
-
2025-09-02 21:24:20
-

- 萍乡融入长株潭都市圈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共赢的必选题
-
2025-09-02 21:22: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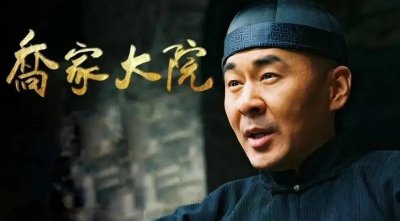
- 清朝巨富乔家:靠贩卖马草发家,有独特生意经,在1953年销声匿迹
-
2025-09-02 21:19:48
-

- 盘点给海贼王配音的60大声优
-
2025-09-02 21:17:32
-

- 《白鹿原》中最美女人田小娥,她结局凄惨因为什么?漂亮?放荡?
-
2025-09-02 21:15:16
-

- 马艳红伏法记:颜值不输女星,被判死刑后凭一句话多活了三年
-
2025-09-02 21:13:01



 女生对你透露感情史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应对
女生对你透露感情史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应对 乔任梁被吊起来的照片(乔任梁被吊着的图片)
乔任梁被吊起来的照片(乔任梁被吊着的图片) 4本都市YY种马文,萝莉控御姐控应有尽有,每一本后宫至少30起步
4本都市YY种马文,萝莉控御姐控应有尽有,每一本后宫至少30起步 《古惑仔》洪兴14位老大,你最多记得10个,后面4个你一定不记得
《古惑仔》洪兴14位老大,你最多记得10个,后面4个你一定不记得 呼兰大侠就是杨中山呼兰大侠案真实情况
呼兰大侠就是杨中山呼兰大侠案真实情况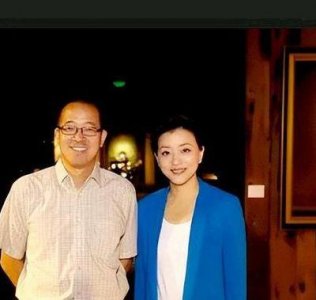 俞敏洪妻子照片(俞敏洪的婚史)
俞敏洪妻子照片(俞敏洪的婚史) 收音机十大名牌(收音机十大名牌第一名是谁)
收音机十大名牌(收音机十大名牌第一名是谁) 20款棒针编织帽子,非常好看又实用,织女们收藏!附10款图样
20款棒针编织帽子,非常好看又实用,织女们收藏!附10款图样 杨子父亲(杨子父亲最新消息)
杨子父亲(杨子父亲最新消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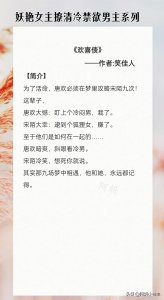 3本妖艳女主撩清冷禁欲男主文:《欢喜债》撩人小妖精x高冷禁欲男
3本妖艳女主撩清冷禁欲男主文:《欢喜债》撩人小妖精x高冷禁欲男